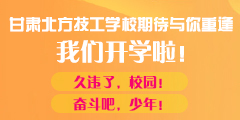中國第十三批援津巴布韋醫療隊隊長、南華大學附屬南華醫院急危重癥醫學部主任鄧立普與學生座談,往事一幕幕展開。
從1975年起,40年來,南華大學共向非洲塞拉利昂、津巴布韋兩個地區派出醫療隊10批25人次,獲得湖南省“援外醫療工作先進集體”稱號。援非隊員們帶去了中國先進的醫療技術,也踐行著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會后,記者走近這群“來自東方的白求恩”。
病房里的上帝
82歲的潘舜華退休在家,茶幾上擺放著一本《友誼的豐碑》,雜志內夾著三張發黃的、四十年前援非時拍下的照片。
1975年,湖南省派出援非醫療隊,南華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原衡陽地區人民醫院)的潘舜華是隊員之一。
來到塞拉利昂,潘舜華看到的是僅有二三十張床位的、破舊的羅蒂芬克醫院。
一位黑人母親抱著孩子來求診。小孩高燒41攝氏度,抽筋,呼吸衰竭,是瘧疾!潘舜華緊急治療,但病情反復,體溫降下去了又上來,驚厥停止了一會兒又開始。潘舜華守了孩子十個小時,病情終于穩定下來。黑人母親撲通一聲跪下來,流著淚說“Thank You”。潘舜華將她扶起,黑人母親將孩子冠以潘舜華的姓,改名為穆罕默德·潘。
“這是你們的中國媽媽!”一個黑人母親指著潘舜華對自己的三胞胎孩子說。他們一家從外省來找潘舜華看病。孩子們都營養不良,潘舜華給他們打血漿,治好了。黑人婦女帶著孩子在鎮上住下來,幾乎每個月來找潘舜華看一次病,瘧疾、拉肚子、感冒……最后孩子們認了潘舜華做媽媽。
潘舜華治好了無數急癥、難診病人。當地醫生說,因為潘舜華,羅蒂芬克醫院的死亡率跟其他醫院比是“小小小小的”。
每一名援非隊員,都用精湛的醫術為病人帶去生的希望。
“鄧醫生嗎?請到急診部協助搶救病人!”第十三批隊員、2013年援津的鄧立普到醫院上班的第二個月,接到搶救病人的電話。
病人嚴重浮腫,呼吸困難。由于體形太胖,心界沒叩出來,肝臟也沒觸診到,當地醫生無法確診。
鄧立普趕到,為病人做檢測。血壓216/112mmHg,心率108次/分,端坐呼吸32次/分。頸靜脈怒張,雙肺少許濕羅音,雙下肢凹陷性浮腫,陰囊水腫。30年的臨床經驗告訴他,患者為高血壓病及嚴重全心功能不全。
清晰的救治方案和步驟呈現在鄧立普的腦海中,利尿,擴血管,強心。“馬上搶救!”鄧立普下達指令。
按照鄧立普的吩咐,電解質、心肌酶學、血糖及肌酐尿素氮血標本送檢;注射加大劑量的利尿劑速尿;擴血管時沒有硝普鈉、酚妥拉明和硝酸甘油針劑,鄧立普當機立斷改用口服的ACE(血管緊張素轉換酶)抑制劑;配好強心藥,拔下輸液器,掐住留置針不讓血倒流,消毒接上注射器。鄧立普輕車熟路操作著,周圍醫生睜大眼睛看,一名醫生豎起拇指:“太棒了!”
“你是中國醫療隊的隊長?”搶救完成后,一名當地女醫生用中文問道。她曾在溫州醫學院實習,“我十分留戀在中國5年的大學生活,看到您今天搶救病人的過程,仿佛回到了在中國醫院實習的場景,嚴謹、有序、規范。”
與鄧立普同一批的龍向陽,所工作的派瑞亞特哇醫院是津巴布韋最大的公立醫院,泌尿外科卻只有3名顧問醫生,醫療設備和水平也十分落后。在龍向陽去之前,由湖南省人民政府2012年捐獻給醫院的輸尿管鏡一直閑置。
龍向陽做的第一例輸尿管鏡下治療是一個腎結石術后病人,D-J管未置入膀胱內,按照以往的治療方式,需再次采取開放手術取出D-J管,創傷大、恢復時間長,病人痛苦。龍向陽采用輸尿管鏡治療,5分鐘便輕松將其管取出,手術室的護士連連稱贊:“龍教授,干得好!”
這是他們第一次稱呼龍向陽為教授,平常他們相互之間只以醫生稱呼。在津巴布韋,教授是尊稱,意味著得到了他們的認可。
更欣慰的是病人的認可。龍向陽在散步時,他診治過的一位患者走上前與他握手,說:“龍教授,你是我的上帝。”
龍向陽曾問當地的花工,“這么多批醫療隊,最記得誰?”回答:戴松。
第二批、1987年援非的戴松,成功完成不完全斷手再植及大面積燒傷植皮手術,在當地引起極大轟動。同為第二批隊員的陳建雄,因醫術高超,被特聘為津巴布韋衛生部顧問,津方設立了“中國醫療隊陳建雄獎”,每隔兩年向成績優異的護校畢業生頒獎。
第九批隊員李天祥說:“我們很受歡迎,不僅所在國的病人、醫生,甚至其他國家在那邊工作的醫生。”有一次李天祥跟一個剛果醫生合作,剛果醫生對病人說:“你很幸運,碰到了中國醫生。”
四十年,援非隊員救治病人總人數無法統計。僅第十三批隊員兩年任期內,共診治門診病人14661人次,住院病人6316人次,手術2473臺次,麻醉2862臺次,接生328人次,搶救危重癥患者429人次,放射閱片31425份,開展醫院科室講座16次,培訓當地醫生和學生396人次。
先進技術為非洲人民帶去了什么?
鄧立普說:“津巴布韋醫療條件差,缺醫少藥,我們國家派出的每一批隊員都是各科室的骨干。當然,僅靠我們醫療隊是不夠的,要把技術教給他們。我把體格檢查法教給我分管的兩個小組的醫生,從此,他們脖子上的聽診器就不再只是擺設和身份的象征。康卯吉醫生在乳腺癌診療中心開展工作,給當地的鉬靶診斷醫生開展培訓;李學林醫生將頸椎手術項目開展起來。龍向陽醫生教他們用輸尿管鏡做泌尿鏡腔手術。尹峰醫生教他們臂叢阻滯及中心靜脈置管……我們還利用講課形式,讓他們了解國內新技術新進展,通過大使館,每年送十個當地醫生到中國學習。通過這些方法,為他們留下了一批‘不走的醫療隊’。”
刀刃上的舞蹈
“如果再讓我去,我還愿意。”剛從手術臺下來的李天祥說。他是第九、十批援津巴布韋隊員。3年援非,他與那邊的醫生、病人、華僑結下了深厚友誼。唯一讓李天祥心有余悸的是艾滋病毒感染者或病患者。
每年,艾滋病大約奪去13.2萬名津巴布韋人的生命。而在醫院,住院病人HIV陽性率高達40%,醫療隊隊員每天都與可能是艾滋病病毒攜帶者或艾滋病患者的病人親密接觸。每一次手術都是在刀刃上舞蹈。
三次援非的劉增華,一次為一個粉碎性骨折病人做手術,助手遞鋼針給他時不小心刺傷他手指,而鋼針上帶著病人的血!劉增華腦袋嗡的一聲,頭皮發麻:萬一病人是艾滋攜帶者呢?
劉增華宣布暫停手術,將手指上的血擠出。這是他第一次碰到這種意外。劉增華命令自己鎮定下來,“事情已經發生了,但病人還躺在手術臺上,多耽誤一秒就多一分風險。”劉增華戴上手套,繼續手術,暫停沒超過60秒。
出于保護隱私的考慮,津巴布韋政府不允許隨意檢查病人是否攜帶艾滋病病毒,醫生只能隨時做好防護措施。
骨科醫生楊俊濤用鉗子幫病人拔鋼針,結果扎破了他戴的兩層手套和手指;麻醉醫生朱志全與醫生一起做人流手術,醫生甩了一下吸引管,管子里的血被甩出來,濺到朱志全眼睛里。脊柱外科醫生李學林兩次遇險,一次刀片劃破手指,一次血濺到眼睛里。萬幸的是,他們沒被感染,他們也沒有因這些危險而打退堂鼓。
劉增華說:“三次援津,我有7次在手術時割傷手指。有一次檢測出來,病人是HIV陽性。說實話我很緊張,等待診斷報告像在等待宣判,這一個傷口可能就改變你的命運。但是我想,因為手術感染上艾滋不可恥。每一個援外的人,都做好了可能被感染的思想準備才來的。每一次手術都如一場戰斗,倘若醫生為救病人而犧牲,沒有恥辱,只有光榮。”
醫療隊在津巴布韋駐地的墻上,寫著習近平總書記總結的援外醫療隊的精神——“不畏艱苦,甘于奉獻,救死扶傷,大愛無疆”。
月光下的離愁
中秋月圓。鄧立普端著酒杯,想著月亮也是這樣照著家里。遠離家鄉和親人,醫療隊員們吞咽下多少離愁別緒。
第九批、2003年援非的楊俊濤出發前往非洲,愛人和5歲半的兒子送他去長沙。路上兒子暈車,無奈返回,楊俊濤只能繼續向前。
楊俊濤每周往家里打一次電話。楊俊濤和中央電視臺原主持人郎永淳長得有點像,電話里,愛人對他說,兒子每次在電視上看見郎永淳,都會對著喊爸爸;有人敲門,兒子立馬跑到門邊,說“爸爸回來了”。楊俊濤笑著笑著,一陣心酸。
家中兩歲的女兒也是李學林的牽掛。每天當地時間下午1點和女兒視頻通話,是李學林最開心的事情。有時深夜想家,他只好一遍遍翻看家人的照片。
李學林每天與家人聯系已是莫大的幸福。第二批援非隊員,想家,但家里沒電話,更不要說網絡。去的隊員中只有隊長陳建雄家有電話,過年時,隊員的家屬集中到陳隊長家接電話,一年僅此一次。第六批隊員朱志全每月給家里寫一次信,從津巴布韋寄出去,要一個月才能到達。去非洲時,朱志全帶了8支牙膏,平均每三個月用一支。牙膏快用完時,他知道,快回家了。
在才到非洲6個月、遠不到“快回家了”的時候,龍向陽“鬧”著要回家。
那天龍向陽生日,隊員一起出去聚餐,喝了啤酒。回來后大家都睡下了,聽到有人在拍打住所的大門。隊友康卯吉起來一看,龍向陽背著包,提著水壺,邊拍門邊喊:“我要回家!我要回家!”
往年生日,妻子做上一桌好菜,一大家人一起熱熱鬧鬧吃上一頓,龍向陽還會和岳父喝上幾杯。而就在生日前不久,岳父去世,遠在異國的龍向陽無法回去盡孝,成為他的隱痛。
得知岳父去世,龍向陽心中焦急,他怕愛人承受不了這樣的打擊,不能操辦好后事。龍向陽打電話回家,愛人對他說:“不用擔心,學校、醫院都派了人到家里來幫忙操持。”
學校及各下屬醫院了解隊員的艱苦與犧牲,積極做好后勤工作,隊員家里有困難,第一時間幫忙解決。
鄧立普家屬反映家中電路有問題,后勤保障部立即派人解決問題;李學林愛人在南華大學附屬南華醫院工作,單位離家較遠,不方便照顧家里的老人和小孩,學校和醫院將她調到離家較近的南華大學附屬第一醫院;逢年過節,南華大學及其附屬醫院人員都要去看望慰問隊員家屬。
當初,他們懷著怎樣的情感去到非洲?
潘舜華接到援非任務時,愛人黃疸型肝炎才出院,小兒子才5歲。她左思右想最后選擇去。“我是孤兒,是國家培養我長大的,支援非洲,為國家作貢獻是應該的。何況國家選中我,是對我人品和技術的信任。”
劉增華也是抱著光榮感去的。第一次去是作為第三批隊員,征集第八批援非隊員時,他又報名。第八批隊員回國時,津巴布韋兩次提交外交照會給大使館,請求劉增華留下來。已經兩年沒回國了,想到再留下來又是兩年不能見到家人,劉增華有些猶豫。
“你代表的是國家,不僅僅是南華大學。而且你還是共產黨員。”南華大學附屬二醫院院長羅志剛給劉增華做思想工作。大使館袁南生大使也說:“劉教授,津巴布韋是我們全天候的朋友啊!”
于是,劉增華又留了下來,并被所工作的醫院聘為科主任,在他的指導下,該院開展的頸、胸、腰椎部手術、人工關節置換等高難度手術在當地和周邊地區產生了極大影響。
蘇小磊要去援非時,母親中風才略有恢復。黨員母親對他說:“作為我唯一的兒子,我不愿意你去。但既然是國家的任務,我也沒什么可說的。我能照顧好自己,你安心去吧!”援非期間,母親再次中風住進醫院,蘇小磊沒有回家,因為:“母親理解我,支持我。”
接到院領導打來的、讓他作為第十三批醫療隊隊長帶隊援津的電話,鄧立普說:“給我點兒時間跟家里商量一下。”鄧立普已年過半百,他怕自己不能勝任。沒想到女兒說:“條件艱苦,卻是一件偉大而崇高的好差事,應該去。”女兒還幫他做好了愛人的工作,于是鄧立普安心離家。
鄧立普不是沒有牽掛。父母謝世,每到清明、春節,他都面朝東方,備上一杯黃酒。鄧立普回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父母墳前祭拜:“兒子平安回國,圓滿完成黨和國家交給的任務。”
龍向陽援非受到兩個人影響。“我讀小學就知道白求恩大夫,知道大愛無疆。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有必要去幫助仍處于水深火熱、缺醫少藥的非洲兄弟們。在科室我是第二個接受這項光榮任務的人,我的楊德敏老師曾兩次援助津巴布韋,我敬仰他甘于奉獻的精神。在那邊,我深切體會到‘國之交在于民相親,而民相親在于常往來’。我們收獲了友誼,贏得了非洲同行和病友的稱贊。回國后我仍與津巴布韋同行保持聯系。我們是醫生,更是友誼的使者。”
南華大學黨委書記鄒樹梁說:“積極支持國家的援非事業,派出優秀醫療隊員并做好后勤工作,我們南華大學做了該做的事情。醫療隊員們在非洲創造了生命的奇跡,也給南華大學的學生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
延伸閱讀:
- ·南華大學援非醫療隊員:來自東方的白求恩(2015-12-08)

 護理專業
護理專業  多媒體制作
多媒體制作  鐵路工程測量
鐵路工程測量  新能源汽車技術專業
新能源汽車技術專業  鐵道類專業專題
鐵道類專業專題  幼兒教育專業
幼兒教育專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