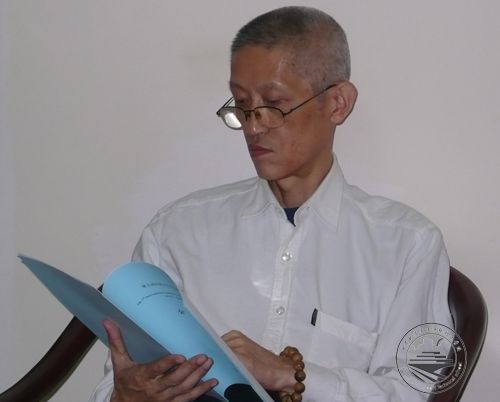
認真閱讀的李小凡。(資料圖片)
他的生活與他的事業(yè)都跟熱鬧不沾邊。
北京大學中文系名教授輩出,他沉默訥言,在其中并不起眼。日常與他說話,總感覺他的回答要比預想的時間慢半拍,話語簡潔到幾乎不會多說一個字。
他的研究方向是漢語方言學,在這一領域,他是全國有名的專家。可是,上網搜索,你幾乎找不到多少跟他有關的條目。
李小凡,北大中文系現(xiàn)代漢語專業(yè)方言學帶頭人,連續(xù)22年身兼中文系各類行政職務,做過中文系團委書記、黨委副書記,后擔任中文系黨委書記達10年。2012年,他病倒在方言調查現(xiàn)場,后被確診為癌癥。今年7月,61歲的李小凡因病逝世,告別了奮斗32年的語言學教研一線,告別了他摯愛的講臺。有人慨嘆,“只出學術不出新聞”的教授又少了一位。
他希望樹葬或者海葬,不開追悼會,不搞告別儀式,甚至沒留下一塊可供師生憑吊的墓碑,他留給大家唯一的東西是他的為師之道、為人之道。
超常的冷板凳功夫
方言學研究是語言研究中最基礎的方向,屬于冷專業(yè),但對于維護我國地域文化的豐富性、語言的多樣性等都具有重要意義。這正是李小凡畢生致力的方向。
方言學研究,需要做田野調查,用國際音標記錄語音,進行語音測試和實驗,收集分析數據。外人看來,這是枯燥的。從1984年起,李小凡每年暑期都要帶領數十名學生,遠赴全國各方言區(qū),開展為期一個月的漢語方言調查實習。他不僅帶學生記音,還要操心經費籌措、當地發(fā)音員的安排、團隊的食宿出行等。
為了確保方言的“純正”,調查多在偏遠地區(qū)進行,而且正值酷暑,條件十分艱苦。與李小凡共事20多年、同一教研室的項夢冰老師回憶說,有一年在杭州調查,高溫難耐,記音時手心不停冒汗,都把方言調查表洇濕了。項夢冰和李小凡住在學生宿舍里,舍管員都看不下去了,問:兩位教授要不換一個有空調的地方住?李小凡答:師生同吃同住是方言調查的傳統(tǒng)。
李小凡的博士生、后來成為同事的陳寶賢無法忘記去廣東潮州的調查:那是2011年6月底,北京遭遇10年來最大的暴雨。因大雨影響交通,師生趕到車站時,火車已開走。李小凡拿著一沓30多張火車票,多方爭取,改簽成功,但已無座位。57歲的他跟年輕人一樣,擠在逼仄的硬座車廂過道中,有人讓座,他堅持坐在自己的行李箱上,顛簸20多個小時。這樣的情景,在過去交通不發(fā)達的歲月更是家常便飯。就這樣,年復一年,跑遍大江南北,從不到29歲的青年助教到兩鬢斑白的博士生導師,李小凡一做就是30年。
同事溫儒敏問李小凡:年年都要去調查,煩不煩?李小凡說,每年調查的區(qū)域對象有別,可以開發(fā)許多研究題目,而且對語言專業(yè)的學生來說,方言調查是打學術基礎。在溫儒敏看來,30年著迷一件事,有教師的責任感,更有學術求真的動力。
北大1955年由袁家驊先生率先開設方言學課程,到李小凡這一代學者,持續(xù)不斷進行方言調查,已積累形成了大規(guī)模的方言語料庫,在全國是獨一無二的,而李小凡就是這項研究最主要的組織者。“都說做學問‘板凳要坐十年冷’,談何容易!可是小凡就做到了。這種沉著堅毅的學問,在如今人人急著爭項目、出成果的浮泛學風中,已成鳳毛麟角!”溫儒敏說。
李小凡在漢語方言的語法、語音、層次等方面都有專深的研究,發(fā)表過許多出色的論作,但他還是格外看重教學。李小凡耗費10年,主持編著了《現(xiàn)代漢語專題教程》《漢語方言學基礎教程》兩部教材。在現(xiàn)行學術評價體系中,發(fā)表文章最被看重,而教材編寫往往不能當作成果。但李小凡就樂意做這樣吃力不討好的事,只要對教學有益。如今,這兩部教材成為國內教學與研究的標桿。
為強化研究生學術能力的訓練,從2001年起,李小凡發(fā)起組織每周一次的方言學沙龍。為了使沙龍不流于形式,李小凡需要提前閱讀學生的報告,工作量巨大,他卻樂此不疲。沙龍有時候一開就是4個小時,最后由李小凡做“總點評”。“從行文到框架結構、思路、觀點,他的點評最詳細、最到位,總能擊中要害。”博士生趙媛說。
沙龍并不計入教師工作量,但李小凡堅持了10多年,沒停過一次。
無論學術還是教學,李小凡坐冷板凳的功夫和堅毅讓很多人佩服。“不管做了多少努力,他的人與他所從事的研究一樣,注定不會大紅大紫。這就是學術的宿命,既然當初選擇了,你就得一生默默接受。”北大中文系系主任陳躍紅說。
一只令人敬畏的手
在風云變幻的改革開放大潮中,李小凡帶領中文系應對了市場經濟沖擊、大學生就業(yè)制度的變化、人事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等挑戰(zhàn)。他與歷屆領導班子確立了“守正創(chuàng)新”的發(fā)展方針,平穩(wěn)推進以學科和人才隊伍建設為中心的各項工作,屢獲表彰。
溫儒敏擔任北大中文系主任時,李小凡曾有過5年和他搭檔。溫儒敏說,小凡大量精力都用來處理系里各種人事、后勤及學生事務,“他對學校工作有不同看法,或者發(fā)現(xiàn)了什么偏差,總是直言指出。他做事的原則性很強,但從不將自己的意見強加于人,也從不做任何以權謀私的事。這些都是讓師生敬佩的地方”。
當學校某些重大決策與中文系實際狀況有明顯偏差,在多次反映無效的情況下,于特定的票決場合,作為學校黨委委員和中文系黨委書記的李小凡,毫不猶豫地行使了一名黨員的權利,舉起了投反對票的手。事后多年,還有當事人回憶說,這是全場幾乎唯一投反對票的舉手,一只孤獨的但是令人欽佩的手!
李小凡去世的第二天,北大中文系正好舉行畢業(yè)典禮。在典禮上,陳躍紅以“李小凡學長”幾十年的人生經歷告誡畢業(yè)生“認真做人”,“做人當如斯,做事當如此。請大家記住這只中文人的手!”
李小凡身上具有強烈的北大情懷,甚至在遺言中也主要是對中文系發(fā)展的建言獻策。他幫助系里籌集資金,按照規(guī)定,系里提出給予他一定的獎勵,他堅決拒絕。同事們從來沒聽到過他一句怨言,也沒聽到他關于付出和回報的感慨。也許就像他的外表看起來的那樣,他過于木訥,對名利得失看得很淡。
溫儒敏說,有的老師當了院系領導便脫離教學,甚至要“撈一把”,而李小凡幾十年的付出,按照世俗來看,他可是沒有“撈”到什么,但他感到心安,對得起“為人師表”這幾個字。
李小凡生前僅有的幾次接受采訪時,說了一句話:“老藝人們常說,‘戲比天大’;對于教師來說,‘課比天大’。”
“課比天大”,是李小凡不經意說出的一句話。在他身邊的同事、學生看來,這是李小凡發(fā)自內心的想法,一個很自然的教師的信念。要不,很難理解李小凡為何面對病魔仍然一如既往對待教學。
2012年,原本身體不錯的李小凡在湛江帶隊做方言調查,突發(fā)胃出血。回校后又有已經安排好的工作要做,就拖著沒手術。半年后,再次胃出血,切除了三分之二的胃。項夢冰回憶,學校原本給了他兩年時間調養(yǎng)身體,他堅持留在一線,除了田野調查,其他照舊。“方言研究”3個小時的課,他還是滿滿當當地上完。2014年4月,李小凡被確診為低分化腺癌,整個胃部被切除,術后他還堅持評閱學生的論文。
為了參加自己博士生的論文答辯,李小凡特意把腹水引流手術推后一周,大家勸他不要參加,但他拖著病體去了,之后又強努著和學生一起照相。當日下午,他就住進醫(yī)院,一去就再也沒有出來。
“誰也勸不動他,他不該那么拼。”項夢冰嘆了口氣。
生命作證,結局如初
生于蘇州、也研究過吳語的李小凡有江南文人的那種細致儒雅,喜歡穿白襯衣,扣子總系到最上面一顆。語速慢,但總能說到點子上。有同事說,小凡是個敏于行而訥于言的人,跟他聊天甚至覺得有點沉悶。
“怕給別人添麻煩”,記者采訪到的同事或者學生都不約而同地提到李小凡的這一點。
陳躍紅說:“做人最高的修養(yǎng)和美德,就是不給別人添麻煩,那么我可以毫不猶豫地證明,李小凡就是這樣的一個人。”住院期間,李小凡和他的家人積極配合醫(yī)生護士的工作,從不提特殊要求。北京大學腫瘤醫(yī)院副院長、消化腫瘤內科主任沈琳說:“李老師和他的家人,是我們這些年見到的最聽從醫(yī)囑,最好交流,又最不給醫(yī)生護士找任何麻煩的病人。李老師到哪兒都是一身正能量。”
李小凡的博士生黃河回憶起導師生病后,自己跟老師的一次接觸。今年三四月,他回江蘇進行畢業(yè)論文的預調查,一回來就找導師商量畢業(yè)論文。導師短信回得很簡單:3點半到我家。黃河不知道那時導師身體已經很不好了,在跟導師暢談了兩個多小時后,李小凡說,我該回醫(yī)院了。原來,老師為了他專門從醫(yī)院請假回到藍旗營的家,大夫只準了3個小時的假。老師為什么這么做?黃河說,一是怕我麻煩,藍旗營離我比北醫(yī)三院更近些。二是怕我去醫(yī)院探望而破費。
導師瘦削的身材,深陷的眼窩,平淡的話語,為了學生的一點方便而枉顧自己的病體,外人也無法知道黃河彼時的內心起伏,他也不愿意多談,“有人說我失聲大哭,其實沒有,我和老師一樣,都不是情感外露的人”。
李小凡被確診為胃癌后,醫(yī)院說只有3個月時間。很多同事為他難過、焦慮,而他卻淡定從容:“我能應付”。
溫儒敏回憶今年春季去探望老友時的情景,彼時李小凡胃切除了三分之二,進食困難,非常消瘦,但興致還不錯,筆挺地坐在椅子上聊天。臉上還是那種柔和而淡然的笑,讓人溫暖,又有些心酸。他顯然知道回天無力了,但反而已把生死置之度外,變得那樣澄明冷靜。溫儒敏說,本來想去安慰他,卻反而感到語言的無力。
李小凡在病重期間提出“干干凈凈地來,干干凈凈地走”。他去世時依然穿的是平時的衣物,質本潔來還潔去。
李小凡,他幾十年所做的事情和他的名字一樣,瑣細,微小,平凡,完全不引人注意。他的人生原則平實無華,就是“老老實實做人,認認真真做學問”,一生堅持,貫徹始終,生命作證,結局如初。
延伸閱讀:
- ·師者本色豈容任意涂鴉(2017-05-03)
- ·為師者,當心存敬畏(2017-09-29)

 護理專業(yè)
護理專業(yè)  多媒體制作
多媒體制作  鐵路工程測量
鐵路工程測量  新能源汽車技術專業(yè)
新能源汽車技術專業(yè)  鐵道類專業(yè)專題
鐵道類專業(yè)專題  幼兒教育專業(yè)
幼兒教育專業(yè) 





